
没有一支俱乐部像圣保利这样固执地满足自己的渴望和要求。
在这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足球俱乐部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那种永不过时的倔强,更有曾经无数个年轻躁动的夜晚,自己迫不及待向往美好的叛逆理由。
这就是圣保利。
文 /朱渊
1960年8月16日清晨,一辆严重超载的绿色面包车从英格兰默西塞德郡缓缓驶向英格兰东部的哈里奇港。
车上包括司机在内共挤了10个人,其中5人是乐队成员。在彼时高度内卷的利物浦酒吧街,这支名叫「采石工人」的乐队根本没有像样的演出机会。为此他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前往当时的欧洲「欧洲夜生活之都」德国北方城市汉堡试试运气。
汽车转轮渡,轮渡转火车,火车再转大巴,一行人抵达目的地,位于汉堡市圣保利区绳索大街(欧洲第二大红灯区)的因陀罗俱乐部。
酒吧老板「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工业风的宿舍:一间紧挨着厕所、散发恶臭和冷气的储藏间。宿舍没有被子和枕头,乐队成员们冷了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英国国旗披在身上。
酒吧老板每天支付给乐队30德国马克,要求他们每晚演出7个小时,但往往收场时天都亮了。在这片霓虹闪烁的红灯区,乐队很快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观众:妓女和身无分文的醉汉。
演出了几晚后,这几个年轻人决定给乐队换个名字——The Beatles披头士乐队,由此诞生。

1960到1962的两年间,披头士在圣保利区举行了大大小小281场演出,他们在这里「从男孩变成了男人」(约翰·列侬语),在这里遇到了日后的新鼓手林戈·斯塔尔,也同样在这里他们逐渐确定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和标志性发型——没有圣保利,就没有披头士。
而圣保利足球俱乐部,也因披头士的到来,拥有了属于自己独特的球迷文化:每个主场比赛前,圣保利球迷会唱着披头士的歌曲,高举带有骷髅图案的旗帜,浩浩荡荡地穿过绳索大街来到米勒门球场。
下赛季,披头士的歌曲也会再次在德甲舞台上唱响。


信仰与政治符号
圣保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相比之下,他们的同城德比对手、完整代表这座城市的汉堡,反而比他们名气更大。在球队114年的历史中,总共只有8段征战德甲的经历,最近一次还要追溯到2011年。
大部分中国球迷听闻或了解这支球队,主要还是通过前国脚、德甲传奇球星杨晨。2002年离开法兰克福参加韩日世界杯后,杨晨曾短暂效力于当时正处于德乙联赛的圣保利效力,一个赛季联赛出场20次攻入3球,不久便回国结束了留洋生涯。

竞技层面除了本赛季的德乙冠军外,他们的高光时刻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个赛季他们2-1战胜了刚刚夺得世俱杯冠军的拜仁,俱乐部随即发售了一款写着「世俱杯冠军终结者」的纪念球衣——这款球衣虽销量不错,却没能为球队带来好运,圣保利也在那个赛季排名垫底降级。
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500多个注册的球迷俱乐部,甚至在现代足球发源地、当地联赛文化根植极为深厚的英格兰约克郡都拥有球迷会。仅在德国就有超过1100万球迷(相当于德国人口的1/8),季票订购量超过绝大多数其他德甲球队,可容纳29500人的米勒门体育场几乎场场都会爆满。
更神奇的是,1981年圣保利平均每场的上座人数还只有1600人,到了90年代末,这个数字变成了20000。这看上去不可思议的转变,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德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十分不稳定的阶段,右翼势力崛起并将足球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与之相对,向来与右翼势力格格不入的圣保利地区,成了左翼人士的聚集地。

1984年12月,来自汉堡和多特蒙德的新纳粹主义者,用燃烧瓶袭击了米勒门体育场外的平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
作为全欧洲第一个禁止法西斯主义者入场的足球俱乐部,圣保利开始吸引大批厌恶极端民族主义、渴望远离足球流氓的年轻人,渐渐从一家平民俱乐部变成了一种信仰与政治符号。也正是那个时间段,圣保利从原本的港口搬迁到了如今距离绳索大街不到一公里的市中心位置。
时至今日,你仍然可以看到左翼思潮对圣保利的巨大影响。比如球场内随处可见的反法西斯、反性别歧视、声援性少数群体标语,比如一年一度的「圣保利反种族锦标赛」,当然,还有那已经演变成圣保利特有文化标签的朋克音乐。


朋克俱乐部
作为一种自带意识形态的音乐流派,没有什么比朋克更能代表圣保利自由、反叛的精神内核。每个主场比赛,球迷在外大声哼唱着披头士的歌曲招摇过市,一线队成员则会在AC/DC《地狱钟声》的背景音乐下步入球场;而每当球队攻破对手大门,球迷就会跟随着节拍唱起Blur乐队的《Song 2》。
在这里,足球与音乐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2003-04赛季,圣保利一度走到破产边缘,球迷自发在体育场外举办了一场音乐节,筹集到25000欧元助球队渡过了难关。作为回馈,圣保利出资在社区开办了一所音乐学校,其中的一些学员后来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收到了不少演出邀请。
与音乐的紧密连结,让圣保利获得了很多乐队的支持。挪威金属乐队Turbonegro为他们专门写歌,冰岛后摇乐队Sigur Rós穿着他们的球衣巡演,球队那标志性的「骷髅海盗旗」,也出现在不少乐队的专辑封面上。

「骷髅海盗旗」已成为俱乐部的半官方徽章,它最早是由一位名叫「马布斯博士」的神秘球迷带到体育场内,被其他球迷所追捧。为什么称之为「神秘」?
因为他是未经授权擅闯球场、把旗子放进来的,所有的消息都只指向——这个人好像和其他40名擅闯者都住在一个朋克公社里——这种做派很「圣保利」。
在圣保利,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平等,并且博爱。米勒门体育场的北看台上写着「任何人都不违法」的大字,而上面的座位则被涂成两颗心的形状。

2016年夏天,圣保利俱乐部重新装修了球员通道。
这个新的球员通道带着满满的圣保利风格,阴暗,恐怖,暖色调又有些暧昧。球员通道两旁是各色涂鸦,「欢迎来到地狱」的字样醒目可见,整个通道就好像把圣保利区的任意一个小巷子搬进了俱乐部。如此光怪陆离的场景出现在圣保利俱乐部,却丝毫没有违和感。

圣保利也是德国第一家将经营原则写进章程的俱乐部,其中的部分条款包括:
圣保利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圣保利传递了一种生活方式,是体育真实性的象征;
圣保利的哲学是宽容和尊重;
球迷不分高低贵贱,只要遵守俱乐部的规定,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观点;
俱乐部要尽力为球迷争取最适宜的开球时间
如今的圣保利,早已不只是一家风格独特的足球俱乐部,它是朋克文化的一部分,是人们践行理想社会的试验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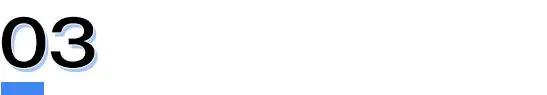
足球俱乐部的另一种可能
对于支持圣保利的球迷来说,俱乐部的存在早就超越了足球本身的含义,成绩自然也不再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球队即使一度跌入德丙,依然能保持全欧洲最高的上座率。
但这种超越足球的狂热,有时反而也会让俱乐部在需要商业化运营的节点遭遇阻碍。
1989年,圣保利曾计划修建一座包含购物中心、酒店的全新体育场,却遭到球迷集体抗议。此后俱乐部的一系列商业化举措,包括增设VIP坐席、将私人包厢出售给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安装一块付费LED屏让球迷畅所欲言,全都在反对声中不了了之。
2017年,圣保利与斯托克城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兄弟俱乐部,同样的港口城市,斯托克以盛产绳索闻名、历史悠久,而且时任斯托克城主席彼得·科茨始终支持左翼工党。但仅仅过去了2年,双方就以人事变动为由宣布合作终止。
背后的真相则是,圣保利球迷不能接受球队与博彩沾上关系,而斯托克城球衣上的赞助商就是博彩公司——作为一支左翼俱乐部,圣保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对抗俱乐部的过度商业化。

不只是球迷疯狂,圣保利俱乐部还有不羁的教练。
2016年夏天,圣保利签下了前多特蒙德前锋杜克施。不过在杜克施加盟球队的欢迎仪式中,迎接杜克施的并不是主教练利宁本人,而是一个带着面具的替代者。
当时主教练利宁正在度假中,分身无术,于是他突发奇想,他嘱托俱乐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找来一张A4纸,打印一张自己的头像当成面具,假扮自己与杜克施合影。
 左一为带上面具的工作人员
左一为带上面具的工作人员
除了利宁之外,曾为圣保利服役18年的霍尔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是一名个性主帅。他是德国知名足球教练学院海因斯-魏斯魏勒学院09届成绩最优秀的毕业生,曾被视为是能够比肩克洛普的一代名帅。
但如今结束了教练生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足球兴趣全无,在汉堡专心经营着一家连锁超市——他说,执教过圣保利这样的球队,恐怕再也无法从其他球队身上找到执教激情了。

《时代周刊》曾经这样描述圣保利:「没有其他的俱乐部像圣保利这样固执地满足自己的渴望和要求。俱乐部民主开明,听从会员的意见。扎根于地区,代表这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地区。团结一致,并不是毫无顾忌地完全以竞技上的成功为导向。这就是圣保利。」
也许圣保利永远无法成为人们口中的豪门球队,哪怕下赛季升入德甲,其首要任务也是保级。但在金钱决定游戏规则的大环境下,他们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足球俱乐部运营的另一种可能。
圣保利渴望被关注,希望被理解、梦想能改变世界,在这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足球俱乐部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那种永不过时的倔强,更有曾经无数个年轻躁动的夜晚,自己迫不及待向往美好的叛逆理由。